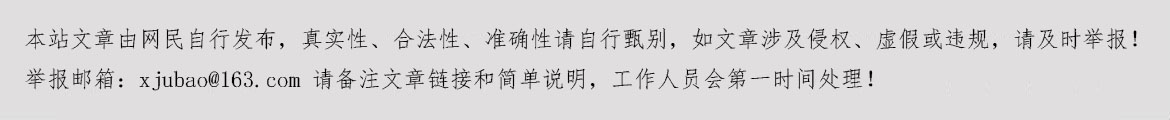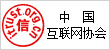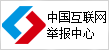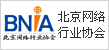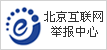“明明生活那么好,还在抱怨什么?”
2022-01-25 11:59:09
文 | 李厚辰
前段时间,有两项与游戏相关的,堪称黑色幽默的“修改”在互联网上流传。
一项是某手游将对话中的“瘟疫”都修改为“痔疮”,便出现了“人心比痔疮更可怕”等让人哭笑不得的台词。而游戏《巫师之昆特牌》,也专门针对大陆市场做了图像的修改。这样的特殊设计,其实从2017年这个游戏上市以来就一直存在,这次却引发了许多核心游戏玩家之外的关注。
这些事情能“出圈”,实在是因为其粗暴荒唐。对原图的改造,全然不考虑表意的完整与基本画面的逻辑,因而闹出像“勺子捅人”这样足以让人发笑的图像。
不过如果只是指出这样特供图的荒唐,是不值得专门用一篇文章讨论。问题需要被引向分歧可能产生的地方,然后我们可以获得新的共识。
这种粗暴而荒唐的内容控制,没有它看上去那样简单,这背后涉及一种当下常见的思维:即精神上的“以形补形”。
01.
无处不在的“特供”
除了广泛存在于游戏行业的,针对暴力和血腥的修改,与此相似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陌生。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其简单,类似“精神以形补形”的思维,似乎看到画面、读到词句,就会产生类似的想法。一种最简单的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。
玩暴力游戏就会引发人的暴力和攻击倾向么?是不是与暴力的画面接触越多,人的攻击性想法就越多?如果这种说法有道理,那么《昆特牌》的画面设计,不就是延续着同一种思路。
不仅是画面,用词也是如此。在电视与网络视频、音乐选秀节目中,有着大量针对歌词的“修正”,例如“给我一支烟”,改为“给我一只眼”,这可能因为谐音还不影响演唱,但将“爱恨都任你颠倒,全世界陪你堕落”改为“你正将水面颠倒,浮出该有的自我”,恐怕就要和歌曲前后词不达意了。
听到悲伤的歌词就会更容易悲伤,听到放弃生活的歌词,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放弃生活吗?早年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一首“禁曲”的传说,即可怕的《黑色星期五》,据称这是20世纪早期一位匈牙利作曲家谱写的曲子,在欧洲导致大量听众轻生,因此欧洲各国联合封禁了这支曲子的乐谱。
与此非常类似的,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对文艺作品的看法。即很多家长认为要限制学生在青春期阅读太宰治等“日本作家”的作品,因为他们的作品将导致青少年罹患严重的抑郁症风险。同样也是出于一种”精神以形补形“的逻辑。
但就在两三周前,网上流传着一封初二女生的遗书,里面写道“毁掉一个人很简单,只需要毁掉她的童年”,令人扼腕。但马上就有很多人申明,所谓按照“国际通用惯例”,不可以在网上传播轻生遗书的全文,因为这样的文章会导致其他人轻生的风险大增。如此看来,这和阅读《人间失格》导致轻生抑郁,有什么区别呢?
更不必说在更大的社会中,一直对社会公共事务有轻批判、重肯定的论调。认为批判使社会退步,而肯定使社会“蒸蒸日上”。
由此可见这种“精神以形补形”,可不是简单的,仅仅只针对一两幅暴力画作的修改,而是弥散在整体文化中的一种倾向。
《弗里达》
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最捡懒的方法,即“分级”,认为分级解千愁,将这种限制手段全数推给未成年人,好像成年人世界的自由就获得了保全。
且不说这里的发心到底是为了“保护未成年人”还是为了“保护成年人的自由”。我认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,分级制度的可行性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,虽然分级可以很好地解决暴力、情色等显性要素,但“悲观”“郁结”,恐怕不是依靠分级可以解决的问题。
我们需要对“精神以形补形”给予一个彻底的认识。
02.
“精神以形补形”的基础,感受的任意性
之前我们有很多文章讨论社会共识的形成,大家都感觉几乎无可能。而说到影响和改变他人,这也是很多人几乎都立即放弃的领域,那么人的思想怎么可能在一两部作品、一两首歌,甚至一段文本中就出现剧变呢?
“精神以形补形”这个词汇看上去简单荒唐,但实际上并不是。在今天这个普遍认为“道理”乏力,道理无法实现说服的环境下,我们会相信两种令人改变的方式,一是“顿悟”,二是“心理学机制”。
前者是小说和电影最喜欢塑造的情节,主人公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总是被微小的事情启发和影响,这是极端浪漫主义的,例如《心灵奇旅》这部令很多人感到共鸣的电影,主人公可不就是被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启发和改变吗?如果这些真的是可能的,阅读一部小说,观看一部电影,甚至短到一篇文章、一个金句,当然会对生活有巨大的能量。
这个词没有看上去那么荒唐,“改变你一生的”后面可以跟随各种不同的名词,也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被广泛地使用。既然我们都寻找“改变一生”的一本书、一部电影、一次旅行、一首歌,并将这样的体验极端浪漫化,那么反过来,当然也可以有“搞砸一生”的一个瞬间或一句话,这自然令人担忧。
除了这样的时刻,我们还相信类似心理学的机制,即一切“非道理”的力量对人的改变,不管是行为主义的,心理暗示的,潜意识的。其“正面形式”,是类似于瑜伽、正念、积极心理学等样式,那同样,我们也可以设想负面的方式。
这样看来,《昆特牌》卡面图画的特别设计,不过就是避免不良心理暗示。而父母禁止子女阅读日本文学,是避免这种文化对人的“戏剧性”巨大浪漫影响,这和禁止轻生文本在网上流传,也是一样的逻辑。如果我们接受浪漫主义式的,“心理学”式的改变,就要接受文化与内容审核修正。
这一切都从一种不协调开始,生活中总是有很多不如意和痛苦。过去,宗教的方式让人接受痛苦,想到未来或超验的结果,能让现在的痛苦有点意义。
但从启蒙运动开始,我们似乎越来越相信自己有一种“经验的自由”,“想法”与“生活”不一定要协调,生活很痛苦,但可以将其“理解”或“感受”得很起劲,我们的精神世界有某种任意性,或是某些短暂的“火花”就可以点燃我们的整个生命历程。
这当然塑造出比宗教诱惑力大得多的生活图景,也就是无论你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,你都可以感到幸福。可以把心理学当作德国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技术化和科学化,为这个宏愿提供一个更可操作的手册与方式。就像一句“多元审美”,就可以让所有人不管环肥燕瘦、长相如何,都能放下外貌焦虑。
《秘密》
但一旦相信精神世界的任意性,那就必须接受硬币的正反面,我们当然可以依靠此种方法让“生活明明很糟,却还可以感到幸福”,那就也可能出现“生活明明很好,但却感到痛苦”。
这样的东西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物理学对象——“能量”,不管是针对文化,针对心态,还是针对“积极心理学”在人精神中积累的东西。我们发明了这个真正决定我们“感受”的东西,能量分为正负,而不是生活本身,能成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内容。
这不仅是一个个体的“理解”,却也可以是一种公共的感受,比如在家庭或亲密关系中,说“明明生活很好,没问题,但你非要多想”,或者在更大的社会中,“明明一切都很好,但你们这群人非要觉得不好”。
生活的实质问题,立即变成了“想法”的问题。那么靠调控与管理涉及“想法”的作品和文化,便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一种针对想象,而非针对真实,通过理解和感受的任意性及其技术,以及所有对“正确感受”的要求,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象,不仅仅是文化审查。因为我们即便逃离了文化的“负面”审查,也会在构造自己的“感受任意性”中迷失,迷失在“诗与远方”“活在当下”“听从内心”之中,这是些比太宰治更为可怕的东西。
因为更可怕的从来不是“坏感觉”或“生活困境”,生活怎么会没有困境呢?
03.
“感到不错”是好生活的底限吗
不管是我们自己觉得状态不错,要激励自我,多交积极夸赞的朋友,远离喜欢批判抱怨的朋友;还是父母认为子女应该更好地理解生活,少看太宰治川端康成;还是主管单位认为社会需要更多正气,所以节目不要歌唱悲伤和死亡。
在这里,我们认为问题是“坏感受”,只要感受不坏,生活就不错。那么谁需要帮助呢?自然是“自觉”生活过得不好的人。但真的如此吗?
一个自觉生活不好,因而郁郁寡欢的人更需要帮助;还是一个自觉生活无比幸福充实,充实到要到处指手画脚,指点他人生活之糟糕,更有甚者还要积极介入,去“惩恶扬善”的人,更需要帮助?
这取决于我们理解的“生活底限”是什么,以及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基本要求。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“感到不错”,而“感到不错”是一个正确的公共感觉,如果又相信精神世界塑造感受的任意性,搞些“精神以形补形”自然不在话下。
但如果这种境况需要以贬低他人为代价呢?尤其是如果贬低的还不是生活中实际认识的人。
也就是说,这种“感受的任意性”总会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把他人想象得足够坏,要么就是塑造“别看他光鲜亮丽,其实满身脓疮”,要么就是“别看他光鲜亮丽,都是巧取豪夺”,这真是两种塑造“感受”的不二法门。前者捍卫了“真实”,后者捍卫了“道德”,不仅“感受不错”,还与真理发生了些关系,这不就感觉更不错了?
所以生活的底限是什么?是面向自我,用尽方法让自己“感觉不错”吗?还是面向他人,重要的是同情心呢?我们需要的是“感受”的介入,还是“同情心”的介入?当然,这里同情心指的绝不是和自己最相似的人共情,而恰恰是与异质性的人和群体,因为对与自己最相似的人充满同情,大概也就是顾及另一种“感受”。
《驾驶我的车》
为何我会主张面向他人的同情才是生活底限,其中原因不少,我们可以先从“精神以形补形”开始。
我想大家都知道,很多时候导致人的感受崩溃的,并不是“感觉不好”本身,而是其他人的要求,不管是父母、老板、男女朋友,还是更大的力量告诫你,“你现在很幸福啊,怎么生在福中不知福”。现在不是生活的问题,而是你自己“感受”的问题,你“应该”感到很好。这才是令人崩溃的一面。
而如果我们拥有同情心,则至少感兴趣的是人的生活困境,而非感受的异常,同情心就能让我们减少许多这种“感受的逼迫”。
其次,在这个土崩瓦解的环境中,真正带来生活问题的,就是一种巨大的同情心丧失,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生活困境有无限的不包容,因为他们赚钱多,因为他们曾经有罪,因为在想象中他们憎恨构陷我们,因为他们愚蠢,因为他们既得利益,甚至最简单的。因为他们过得比我们好。
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停止一切同情,为当下的伤害辩护,不仅辩护,还对任何形式的伤害喝彩叫好。这才是让我们生活失序的重要因素。
我们不仅已经体认这是“互害社会”,还故作冷静地认为,资源有限,不得不互害,只有进一步的胜利才可以摆脱;或更有甚者认为所谓“人性如此”,互害不可避免。我们放弃同情心,并对同情心再次作用完全抛弃。
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,我们又有什么可能认为自己可以保持“感觉不错”呢?到底有什么样的“精神以形补形”,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让人保持感觉不错?还是其实真正让人感觉不错的唯一方式,就是保持在优势一方,并持续地伤害他人?
所以不管是一个人面对自己,或是一个父母面对自己的子女,恐怕得失算计,和在得失算计上如何动用“精神的任意性”达成感觉不错,都不是这件事的关键。
当然我们也非常明白其中的难度,在一个普遍缺乏同情心的社会,当一个有同情心的人,无论如何都是“不划算”的,在一个大家普遍高度同情的环境,拥有同情心才会有足够回报。
似乎现在保持同情是一种“愚勇”。
04.
人不是一台被指令控制的计算机
这需要我们换个方式看待“感受”。人有自由意志,可以自由作出抉择,但人恐怕没有自由“感觉”,可以好的东西觉得坏,坏的东西觉得好。说到底,最后想做何“感觉”,取决于人怎么抉择他的生活。
今天的人感觉“虚无”,感觉“人间不值”,恐怕和太宰治没什么关系,这是一种现代生活形式内含的价值缺失。在这种生活形式下,看太宰治会觉得心有戚戚,甚以为然;看梭罗会觉得自己永无可能如他一样,好生活是不可想象的;就算是看积极介入生活、功成名就的经历,恐怕都觉得和自己无关。
可见人不是一台输入指令就可以控制的计算机。一旦生活形式确定了,ta的想法和感受就已然确定,这个时候看什么都不会有区别,因为康德讲过二律背反,真正有任意性的不是“感受”,而是理解。
人在生活很丧的时候,看积极的东西不会积极,反而倍感压力;而在积极的时候,看消极的东西,反而反衬自己活力满满。感受是一个不可以操弄的东西,生活是什么样,感受就是什么样。
而生活是什么?在现代社会中,生活是最看上去琳琅满目,又一潭死水难以改变的东西。也许正是如此,我们才想要生活不变,感受改变,去搞些“以形补形”的东西,以求速胜。
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,才有我们自己、父母、师长以及更大的权力,来对我们的“感受”提出要求,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一种“生命政治学”吧,权力最终将直接对“感受”提出要求,这已经不是精神的以形补形了,这是以形塑形。生活中常常面临的种种特别设计,就是这个以形塑形的努力。
《祈祷落幕时》
如果这让你难以接受,你能改变的不是形,而是生活。但自己生活的改变又谈何容易,恐怕在这里最容易改变的就是同情心了,依靠对他人生活的真诚观想,以达到拓宽自己生活的可能,这已经是最容易的方法。能抵抗无处不在的“感受的逼迫”,正是同情心。
因为同情心的生活,让你至少可以摆脱两种最糟糕的感受,愧疚与后悔。如果有一种生活是以较少的愧疚与后悔构成,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吧。
文章头图来自《弗里达》,编辑:苏小七。